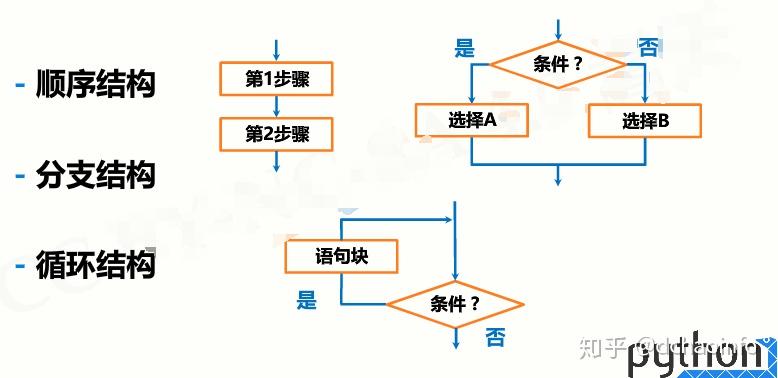非物的反噬
主要参考文献/书目:
- 《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全新名词“非物化”的哲学小品。当人类迈入数字化时代,我们不再面对卢卡奇所批判的物化,而是韩炳哲所提醒我们注意的非物化。非物化让我们被连根拔起,成为不断流转的数据流的孳生物。这是相当可怖的一种说法:我们能够注意到来自物的支配,但是来自非物的支配是内在的、隐蔽的、不显著的;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意识能够证实我们“从一片苦海游向另外一片苦海”。
从物到非物:一种技术意识的启蒙
第一部分:从物到非物,作者以简明利落的文字,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启蒙。
秩序: 作者明确地指出,物构成了大地的秩序、地球的秩序;数字化秩序在今天正在接替大地的秩序:这二者之间的区分是鲜明的:物是固定的、外在的、可预期的、绵延连续的;而非物是依赖于短期刺激的、不持恒的、流变的。非物的存在让整个世界变得幽灵化;变得没有了朴实牢靠的手感[1]。
焦虑的消解: 海德格尔话语中的“此在”寓意着“在‘频繁地’与物‘打交道’”。这里的物指的是韩炳哲所言说的,被动地呈现在面前的“物”。数字化的秩序的目的就是要克服那种被海德格尔理解为人之生存本质特征的忧虑[2]。我们看似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秩序当中消解了曾经本然的焦虑,活在了一种确定的选择当中;我们总是乐于沉浸在这样一种智能的无能之中,而不认为数字化的秩序潜藏的是更大的焦虑。
历史的消解: 历史是叙述性的而非加成性的,它从属于大地的秩序;信息是加成性的、非连续性的单元,它独立于大地的秩序;信息无法组成一段历史,它所组成的我称之为“断点历史的假象”。加成与累积排斥铺陈叙述;只有铺陈叙述才能够奠定意义和关联的基础:数值的秩序没有历史和回忆。信息的膨胀,使得我们日益被塑造成为一种储存器,这种储存器会碎片化我们的映像,甚至消解我们的记忆[3]。
从“乐团指挥”到“智能牢房”: 这应该同时蕴含着两层含义:(一)“虽然它帮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它同时让我们遭受日益严重的监视和控制”[4]。智能设备一次次地深入我们的私人领域。它能够为我们带来完整全面体验,这同时意味着它需要持续地突破我们隐私的边缘。(二)它们能够一次一次地证明自己是性能优良的信息能动机。通过数据的堆砌式收集,它内在地循环强化着自己的算法机能。“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当中,人日益失去了他的行动力,他的自主性。[5]”对数字化乌托邦怀有幻想的人而言,不断膨胀的黑箱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一种稳定性。在这种稳定性当中,世界将迷失在神经网络的深层层面当中,而人无法进入这些人造的层面:我们成了我们造物排斥的对象。
真理的时间: 信息的高流动性吞噬着我们留给真理的时间。忠诚、教养、信任、承诺、责任,这些长时间的实践活动的条件或者产物在信息的流蚀下逐渐坍塌:短期效应成为唯一的正确追求。我认为韩炳哲的这一段话说的平静而深刻:
我们今天追赶着信息而无须获得知识;我们知道一切而无须认识一切;我们四处游历而无需获得经验;我们不间断地交流而无需加入一个共同体;我们保存了海量的数据而无需考察记忆;我们积攒了朋友和粉丝而无需遇到他者:信息就以这样的方式促成了一种无需持续和绵延的生活。[6]
**主体性质的转向:**对物不感兴趣的未来人不是劳动者,而是游戏者。行动的人,他打断现存的事物,将全然地它物放置在世界当中,他必须克服阻碍。游戏者的特征是他脱离了劳动的行动,他根本不需要克服任何阻碍,就能够进行选择,仿佛选择的前身就是他的劳动一样。韩炳哲称之为“游戏飘荡式的轻松特性削弱了人们最先畏惧的那种无所依托特性”,我将之称为“轻松的麻木与虚妄”:游戏的戏谑带来的是精神的解放,这里所谓的解放指的是放弃对于无所依托的焦虑与畏惧:我们彻底地掉入了信息所定义的自由当中。主体,也就是人对那一丝本能的放弃,带来的是主体性质的转向。游戏着的未来无手人是历史终点的化身。
从占有到体验
第二部分:从物的领域到非物的领域,作者分别分析了人、物、非物之间关系范式的转变。
体验与占有: “体验意味着对信息的消费”[7]。我需要复述一遍体验与占有的关系。体验对应的是占有,而存在对应的是拥有。在信息时代,完全臣服于信息的个体更注重的是体验而不是占有,更加注重的是存在而不是拥有。从属关系上——信息是流变的,可共享的,不持续的,因此对信息这一主体谈论“占有”是不恰当的。我占有了一个单位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以某种形式同样占有:在这里,占有的意义被消解了[8]。交互形式上——信息是随时更新的,它不具备随时间逐渐升值的过程。相反,它会不断迭代更新:在这里,个体注重的是短时间内信息的获取和感知。人与信息之间不能够建立起长久的亲密的关系。正如文章中所说那样:
忽然之间,保留在物中的回忆不再具有价值。回忆让位给新的体验。今天的人们显然无法留驻在物当中,或者无法让物活化为他们真切的陪伴……它们(指关系)削弱了体验的可能性,即削弱了消费主义意义上的自由。[9]
存在与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抵牾的:信息以其自身短暂性、时效性的缺乏存在的稳定性;“信息的宇宙论不是存在的宇宙论,而是偶然的宇宙论。” ↩︎
参见[美]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第7页。 ↩︎
我认为“被消解的记忆”在这里是一种恐惧的主要来源。我们是否还真的能够熟习地叙述出属于我们的历史?我们是否能够讲出比浅显易得的信息更深刻的一些内容?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信息,并且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就是我们记忆的全部。它没有意义,它不能关联更多的价值。 ↩︎
参见[美]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第9页。 ↩︎
参见[美]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第10页。 ↩︎
参见[美]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第13页。在这里,我找到了一种呼应作者的可能:既然信息带给我们的不是安定生活所需要的长时间实践,那我们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时间策略。这能否被还原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超脱于信息流的完全面向内在的规划或者是目标? ↩︎
参见[美]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第21页。 ↩︎
占有最显著的特点应该是排他性,但是信息作为信息时代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其本身已经对占有的这一特征构成巨大的冲击,因此在这里我认为,占有的意义被消解是必然的过程。 ↩︎
参见[美]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第22页。 ↩︎